[隨筆]沉溺之死
- 烏鴉
- Dec 18, 2017
- 4 min read
就像是一條金魚,被從魚缸中一把挑起,暴露在氧氣之下。過不了多久,或許是十分鐘,亦或是五分鐘,他終究會從掙扎回歸平靜,而根本不會有人在意,那條魚是怎麼出現在桌子上的。無論是被重摔還是被輕放,他終究會逐漸衰弱,小巧的心臟鼓噪著,越來越激烈、越來越費力,接著在他生命的最終,在那最後的一瞬,跳動的鼓聲將從此噤聲不語,那條魚會將直挺地平躺在桌子上,濕軟的身體將逐漸僵硬,腐臭將覆蓋過魚腥,像是被白蟻蛀蝕的腐木,接著被氣體填滿,逐漸膨脹,臭氣將汙染桌面,他們或許會因為嗆鼻的氣味而皺起眉頭,但不會有人去在意那一條魚是怎麼出現在桌子上的,因為那並不重要。
但說到底,那也只是個假設,或許在金魚在掙扎中會翻落到桌底,最終成為沒有人能夠找到的未知臭味來源之一,又或許在僵直之前被路過的人丟回水裡。能夠產生的變因太多,或許他需要換個更大一點的桌子,或者他應該要把魚缸給藏在櫃子深處,又或許直接把缸裡的水倒個乾淨。因為,一切的假設都要經過驗證才能成為事實,而實驗恰好就是這個假設最好的驗證方式。但是即使一切都準備妥當,假使實驗成功了,但那也不能夠說明甚麼,他需要更多條魚來佐證這個假設,單單一條金魚的樣本數過於稀少,或許他需要進行上百次的實驗,但這樣做又有甚麼意義,這個假設從根本上就沒有意義,或許他應該換個實驗對象,或許他應該要從人類本身開始實驗才行。
但要拿誰來實驗就是個問題,或許他應該要先縮小範圍,全球的人口數過於龐大,而每個人與人之間的親疏遠近皆有不同。費格是他的男友,所以他不會放任他躺臥在角落,像是條離水的魚掙扎著吸取著氧氣,但如果需要,軍方隨時會將他從魚缸拉起,丟入戰地,或許他會跳回缸裡,亦或跑到河裡,但也或許會跳動在桌面上,在僵直後用國旗覆蓋惡臭;或是跌入桌底,然後空著的木箱子裡就會放著幾件個人衣物,成為他的遺體。所以除了魚,他還要定義那隻將魚挑起的那雙手,那雙手應該是個人還是團體,是魚的親友還是陌生人,而上百次的實驗也代表著他需要找到上百條抓魚的手、上百張桌子、上百個裝著魚的魚缸,和上百條金魚。
那麼說到底,他為甚麼要開始這個實驗?魚的存在是脆弱的,在這間破敗的屋子裡,除了他跟費格就再也不會有人經過,這裡已然成為了一座死城。所以何不就直接將他抓起,又或將他踩扁,還是來試驗看看溫水裡的小魚是否會成為青蛙,他的生命或早或晚必將迎來終結,已經沒有人可以餵他了,那麼或許對於那條魚而言,上天最後所能給予的慈悲,就是一場快速的死亡。
塔爾的雙手顫抖。他能預想到小魚滑溜的身軀,最開始魚尾會掃過指間,而包覆魚身的手掌能夠感覺到小魚的掙扎,但是金魚的力道太過渺小,所以他必須小心翼翼地避免將魚抓成一團肉泥。但又有甚麼關係呢?如果抓魚的目的就是要製造他的死亡,那麼或許直接在水裡捏死他,才是最省力的結局,反正也不會有人在意一條小魚的生命,他會腐臭還是膨脹,這都不重要,他就是一條小魚,一直在水裡轉圈,沒有目的也不會有目標,對於世間萬物而言,渺小如同塵埃,就算他在這缸水裡發臭腐爛,身軀長起了毛邊,最多也只會導致路過的生物摀鼻皺眉。
塔爾突然感到噁心,胃酸竄上了胸腔,燃燒著食道,苦澀了口腔,他突然發現四周圍照著的空氣變成了水,而缸裡的金魚不在,四周的地板變成了裝飾用的小石子,一邊的牆壁成了水草,而天花板則變成了一個模糊的開口。開口之上有著人張開的手,他看見了自己把手伸入缸底,感覺到冰涼的水流淌過他的手臂,而他也看見了自己被那雙大手環繞,就像是被蛇群纏繞住胸口,壓迫著胸腔,他的臉部發燙,耳邊能夠聽見心臟正尖叫著快要窒息,他感覺到自己的手掌正在慢慢收緊,同時被擠壓的肋骨發出了清脆的噪音。
「我這邊找不太到甚麼吃的,不過還好櫃子裡有放著一些泡麵。」費格的聲音打斷了塔爾的思考,「你去看過廚房了嗎?」他輕拍了塔爾的肩膀,接著隨手拿起一旁的魚飼料,餵給了在缸裡悠游的金魚,「走吧,塔爾,我們一起去找廚房。」他牽著塔爾,往一旁的房間走去。塔爾隨意地附和著,他跟著費格向前,雙眼卻仍舊望著金魚出神,小魚狼吞虎嚥地吃著久違的飼料,一旁的櫃子卻仍舊有氣泡漂浮。
他還在水裡。
(完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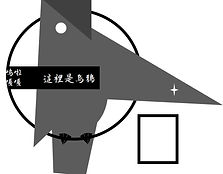
Comments